西方正在品尝误解普京长达20年的后果 | 政治 | 半岛电视台
在过去8年的时间内,俄罗斯总统普京第2次强行重新划定乌克兰边界,并将其部分领土面积(相当于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面积的总和)并入俄罗斯,然而,西方并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假装震惊。
我经常看到西方人抱怨普京是一个性格不明、难以预测其行为的人物,然而在过去的20年内,普京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声称有意重塑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边界,但是西方却总是对这种信号不以为然。早在17年前,普京便在向俄罗斯议会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指出,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而在两年后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又在其著名讲话中批评了西方,并且认为北约的扩张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在慕尼黑讲话过去仅仅一年之后,俄罗斯便对其邻国格鲁吉亚发动了攻击,将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分离,作为对格鲁吉亚承诺加入北约的回应,而在此6年之后,俄罗斯又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对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的回应。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对北约封锁的臆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普京对西方的政策,而西方人又是如何误解了克里姆林宫之主的思想。
以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为例,他认为俄罗斯最近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举措,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和对国际秩序规则的威胁。尽管这种描述非常现实,但是却也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谴责了西方——为什么在俄罗斯袭击格鲁吉亚和吞并克里米亚时,西方人未能意识到这种威胁?西方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反应是暂时中断与俄罗斯之间的对话,而又在后来恢复了它与俄罗斯之间的往来。

同样,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也没有严重到足以使之无力再对乌克兰直接发动战争的程度。拜登在去年6月与普京举行首次峰会后认为,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可以建立可预测的关系。事实上,拜登也与前任的美国总统一样,未能摆脱对俄罗斯的有限了解。
2001年6月,小布什在斯洛文尼亚会见普京之后表示,他观察了普京的眼睛,觉得他的眼神非常清澈,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巴拉克·奥巴马也拒绝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举措,视为一个地区大国威胁其邻国的行为,另一方面,唐纳德·特朗普则认为,欧洲在军费开支上的吝啬,远远比俄罗斯的潜在危险更加严重。
西方可以将冷战后和平的崩溃归咎于普京的偏离,但事实上,西方却在助长普京的侵略性并推动他反抗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地缘政治局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正处于不利地位,而普京则操纵着俄罗斯以东地区的地理因素,以破坏其安全结构,并通过将能源供应当作武器的方式,使其经济和公民在今年冬季面临着挨冻的风险。但是欧洲对普京的误解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它没有排斥或制裁普京针对邻国的扩张主义倾向,而是选择了安抚他。尽管欧洲人最近开始制定摆脱俄罗斯天然气的应急计划,但是他们不应该对俄罗斯将能源供应武器化的问题感到震惊。
在从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中,他们品尝了他们在过去数十年来种下的苦果。默克尔在冷战后将深化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为与俄罗斯和平相处的一种方式,这种做法或许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她和其他的欧洲领导人一样,从未意识到让欧洲受制于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风险,甚至是在普京统治早期,对西方表现出仇恨并且渴望重振苏联地缘政治地位之时。
欧盟的成立是一个从二战中迅速恢复并转变为全球经济强国集团的理想模式,但是直到最近,欧洲人才想起有必要变成一支能够单独应对安全挑战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
马克龙是唯一一位公开谈论实现欧洲战略独立的必要性的欧洲领导人,但他并不是因为俄罗斯带来的风险才想起了这种需要,而是因为美国在牺牲法国在太平洋的野心的基础上,组建了“AUKUS”联盟。因此,美国主导欧洲对普京的政策,并迫使欧洲国家增加军费开支,同时放弃与俄罗斯之间的管道外交,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可以将冷战后和平的崩溃归咎于普京的偏离,但事实上,西方却在助长普京的侵略性并推动他反抗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地缘政治局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崩溃本可以变成建立可持续和平的机会,并推动莫斯科与苏联的过去彻底决裂,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西方将俄罗斯霸权的失败,视为进一步扩张北约和根据其利益重塑世界的机会。西方由于在冷战中的胜利而对全世界产生的傲慢,在过去的20年内发酵了一种比冷战时期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新全球形势。
西方在世界上的许多朋友现在都处于观望状态,中俄正合作打破西方的霸权地位,尽管二者属于地缘政治对手而非盟友。北约的扩张是说明西方对普京理解有限的一个明确案例,正是这种扩张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破裂,而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并未出现。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凭借他们的狡黠而成功阻止了核冲突的爆发,但是在今天,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领导人的外交却陷入了停滞,核风险迫在眉睫。在战前,西方试图听从普京,但在帮助他变成一只饥饿的熊之后,西方却又无力驯服。
这场战争虽然悲惨,但是西方需要参与进来,这不仅仅是为了威慑俄罗斯,也是为了弥补在过去20年内采取了低估普京重要性的政策的过失。乌克兰人在为俄罗斯的霸凌行为承受后果的同时,也在为西方未能在早期准确理解普京并对其采取果断行动的事实而付出代价。如果俄罗斯和西方能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那样,以大国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基础来打交道,那么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损失的领土面积会更小;如果西方在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之后能够更坚定地与普京打交道,那么西方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减弱。
有人可能会辩称,沉醉于历史并在这个时代呼吁为新的扩张主义提供民族主义框架的普京,根本不需要太多侵略性的动因来反抗冷战后的和平。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更加明智的做法是承认西方促成了普京的侵略性,并达到了威胁欧洲和平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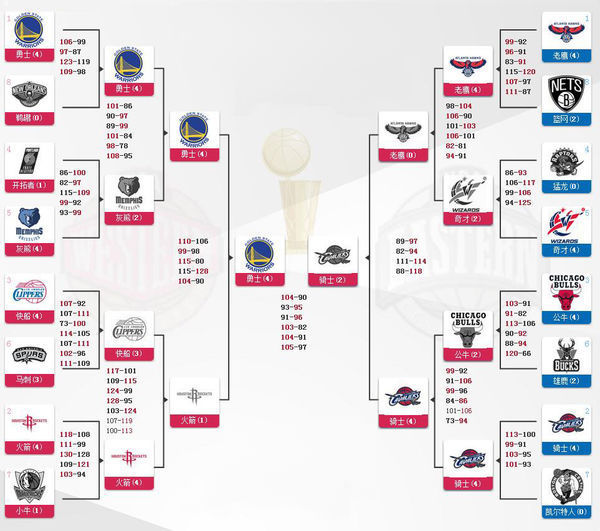
若非特殊说明,文章均属本站原创,转载请注明原链接。
相关推荐
- 优直播:西甲巴萨vs西班牙人免费直播预告 - 哔哩哔哩
-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未来四年禁止俄罗斯参加国际体育大赛_新闻频道_央视网(cctv.com)
- 专访前世界冠军诸宸:一家三口不同身份参加亚运会_京报网
- ■赛场直击揭幕战 宁夏平罗恒利7∶2战胜成都大学_兰州新闻网
- 欧洲杯小组赛最佳阵容:C罗领衔,荷兰三人入选
- Muse来了!歌迷Feeling Good!(感觉良好)_文娱新闻·看点_新京报电子报
- 中国女篮奥运资格赛12人名单出炉 邵婷韩旭领衔_体育_央视网(cctv.com)
- 欧洲杯赛程2021决赛时间(欧洲杯赛程2021决赛时间表) - 欧洲杯 - 技术小zhan
- 欧洲杯中的“黑科技”:中国智造出海抢食|欧洲杯生意经|世界杯|欧足联|乌拉圭队_网易订阅
- 汤爹:詹眉是最佳组合 想成湖人传奇需再夺一冠















